在判斷腸道微生物是否影響人類健康時,很難區分因果關係和相關關係。 分析微生物與人類疾病相關的特徵和習慣的關聯性,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人體中的常駐微生物被稱為微生物群,代表著多樣化的微生物物種群落,包含了由數以萬億計的主要細菌細胞組成的複雜生態環境[1]。 我們的腸道菌群是這些群落中最大和最多樣化的,與我們身體的細胞和系統(如免疫系統)[2]不斷地相互作用,它塑造了我們的健康狀況,也被我們的健康 狀況所塑造。 腸道菌群的特殊組成和多樣性與許多健康狀況有關[3]。 但是,通常不知道這種關聯是否只是相關性還是因果性,或者它們是否可能導致疾病或有助於產生疾病。 解決這個問題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為在健康的個體和患有相關疾病的個體之間,可能存在許多生理和生活方式的差異。 這樣的混雜因素——與微生物群和健康狀況相關的變量——可能是我們觀察到的不同研究結果之間存在許多差異的原因,這些研究將腸道菌群的組成與人類健康聯繫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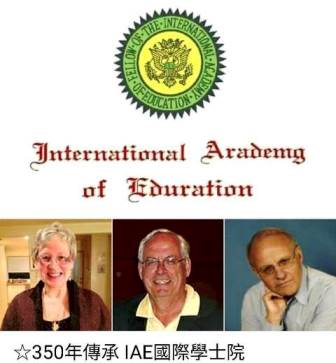
(↑點入)
Vujkovic-Cvijin等人[5]在《自然》上撰文,討論了這個問題。 首先,他們考慮了患有和不患有某種疾病的人之間的生理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並確定了本身可能與腸道菌群的組成有關的差異。 這種差異會導致健康個體和患病個體之間腸道微生物組成出現差異。 如果不了解這些差異,就很容易將生活方式與微生物群之間的相關性和混雜性關聯誤認為是疾病與微生物群組成之間的信息性因果關聯。
接下來,作者嘗試通過一對一的方法,將患有某種特定疾病的個體與在這些潛在混雜因素方面與他們相似的健康個體進行匹配[6],來處理這些混雜因素(圖1)。 比如說,將年齡、性別、體重指數相同的人進行匹配(體重指數會根據身高來評估一個人的體重)。 這種類型的匹配程序經常用於觀察性研究中,在這些研究中,不能將個人隨機分配成兩組,並對兩種不同的情況進行比較。
比較人群來評估腸道微生物和人類疾病之間的聯繫。 Vujkovic-Cvijin等人[5]確定了影響腸道微生物(稱為微生物群)組成的因素,這些因素在有特定疾病和沒有特定疾病的人群中的流行程度不同。 a, 例如,酒精攝入量低的個體比例可能在健康和患病人群之間存在差異。 隨機抽樣比較個體,如果不考慮這個因素,可能意味著似乎與疾病狀態相關的微生物群差異是由於這個因素產生的。 b, 作者比較了在可能影響微生物群的因素方面相匹配的個體。 然而,這種抽樣可能會選擇出不能代表健康人群的個體。
Vujkovic-Cvijin等人報告說,性別、年齡、排便質量(糞便歸類為固體、正常或鬆散)、體重指數和飲酒水平是最強的潛在混雜因素,可能會阻礙確定疾病與腸道菌群組成 之間的真正關聯。 這是因為這些特徵與微生物群組成和疾病狀態都有很強的關聯。 研究患有某種疾病(如2型糖尿病)的個體和沒有這種疾病(但可能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之間的差異時,疾病狀態和不同腸道細菌的豐度之間似乎有許多 統計顯著性關聯。 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上述的一些混雜因素標準對患有或不患有這種疾病的個體進行匹配,其中許多關聯就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 這意味著,以前歸因於某些疾病的一些腸道菌群變化可能來自於與這些混雜因素有關的其他潛在原因。
例如,飲酒會導致腸道菌群的變化,而患有某些疾病的人飲酒量低於平均水平(也許是因為他們服用的藥物)。 因此,如果不能根據個人的酒精攝入水平進行匹配,可能會得出一個誤導性的結論,即與疾病相關的微生物群變化可歸因於疾病本身,而不是低於平均水平的酒精攝入量 。
Vujkovic-Cvijin及其同事的方法可能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提出的一些混雜因素可能與疾病症狀有關,而不是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有關;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混雜類別中的人可能已經 生病,但未被診斷出來,或者即將會發病。 在這種情況下,與健康人進行匹配實際上可能會帶來偏差[8]。 例如,在研究酒精性肝病時,根據人們的酒精攝入水平進行匹配是沒有意義的。 此外,即使潛在的混雜因素與疾病的定義症狀無關,或者與疾病的症狀非唯一匹配,但如果匹配混雜因素意味著最終的匹配組不能代表健康個體,那麼仍然應該引起關注。 例如,將患有肺癌的人與未患肺癌的人進行匹配——重度吸煙的年份相同,將不能提供一個真正健康的對照組。
考慮到這一點,不應該根據排便質量對炎症性腸病患者和健康個體進行匹配,也不應該根據血液中糖蛋白HbA1C的水平對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與健康個體進行匹配;HbA1C提供了 一種評估長期血糖水平過高的方法(作者沒有這樣做)。 研究人員還應該對根據體重指數將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與健康個體進行匹配持懷疑態度。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使用一個較小的隊列重複了他們的分析,其中健康組中沒有一個人自述患有任何類型的疾病(以前對健康人的定義標準只是那些沒有自述患有特定疾病的人 )。 他們發現疾病狀態與生理和生活方式差異之間有類似的關聯,儘管這些關聯現在在統計學上不如原來的分析中顯著,或者不再顯著。 遺憾的是,去除任何自述患有疾病的個體,並不排除將疾病隊列中的人與對照組個體進行匹配,後者可能仍未被診斷出來,或者其疾病狀態可能處於中間模糊狀態;例如, 如果將患有糖尿病的人與糖尿病前期的人進行匹配,就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這個問題的範圍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但是向所有醫學研究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什麼構成健康的隊列?
最後,值得謹記的是,確定腸道菌群組成與人類健康之間的潛在混雜因素並不意味著這些因素是不相關的。 在確實存在關係的情況下,也不意味著缺乏因果關係。 例如,如果飲酒導致微生物群發生變化,進而導致2型糖尿病的發生,那麼微生物群和疾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在匹配個體的飲酒水平後,就看不到這種關係了。 如果炎症性腸病導致的微生物群變化引起腹瀉,並且個體在排便質量上進行匹配,那麼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此,Vujkovic-Cvijin及其同事的結果並不排除微生物群具有因果效應。
微生物群與人類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問題是這一領域的核心課題。 這些發現必將在未來幾年繼續促進該領域的研究,而Vujkovic-Cvijin等人進一步推動了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作者:Sigal Leviatan & Eran Segal
參考文獻:
1. Sender, R., Fuchs, S. & Milo, R. Cell 164, 337–340 (2016).
2. DeSalle, R. & Perkins, S. L. Welcome to the Microbiome (Yale Univ. Press, 2015).
3. Honda, K. & Littman, D. R. Nature 535, 75–84 (2016).
4. Clemente, J. C., Ursell, L. K., Parfrey, L. W. & Knight, R. Cell 148, 1258–1270 (2012).
5. Vujkovic-Cvijin, I. et al. Nature 587, 448–454 (2020).
6. Schlesselman, J. J. Case-Control Studies: Design, Conduct, Analysis (Oxford Univ. Press, 1982).
7. Rose, S. & van der Laan, M. J. Int. J. Biostat. 5, 1 (2009).
8. Costanza, M. C. Prevent. Med. 24, 425–433 (1995).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0-03069-8